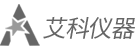|
其實,與不及相對應,如果過度了,也是不孝的表現。 春秋后期,禮崩樂壞,貴族奢侈過度,僭越之風,時有發生。 《左傳》成公二年中的相關內容,就記載了宋文公葬禮“僭越”:八月,宋文公卒,他是宋國第一個厚葬的國君,墓中填滿了大蚌蛤燒成的灰和木炭,寒進了很多的車馬,甚至使用了人殉,而且有特別多的隨葬品。槨的式樣模仿天子的宮室、宗廟,棺則使用了天子才能擁有的裝飾品。諸侯可用車馬,但是有量的限制,文公肯定突破了規定;棺槨的形式像宮室、宗廟的屋頂,是天子的制度,文公享受了,也突破了規定;棺材表面繪制相關的圖案,上面覆蓋著裝飾品,這本是天子的專利,文公使用了,就是“僭越”。 孔子認為,這種奢侈的殯葬行為,盡管表達了對死者的尊敬和愛戴,但卻是一種僭越行為,因此不是孝。 孔子強調,辦喪事,應該節儉,“以其奢也,寧儉。”不重奢華,重在哀戚。“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述而》)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子張曰:“……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都是在發揚孔子這方面的思想。孔子還認為表達哀戚也要適度。《禮記·檀弓上》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伯魚(孔丘之子,名鯉)的母親死了,一周年后,伯魚還在哭。孔子聽到哭聲,問:誰在哭?弟子報告說:鯉。孔子聽了,笑著說:過分了!伯魚聽罷,再也不哭了。母親死了一年,伯魚仍然在哭,孔子認為不符合禮的規定。 孔子一方面覺得“三年之喪”孝,改成一年,不但不孝,而且還不仁了,另一方面又認為殯葬搞得太隆重了也不好,同樣是不孝。孔子的觀點乍看起來好像矛盾,其實不然。 實際上在孔子那兒,殉葬的奢簡并不是判斷孝的標準。在孔子看來,周天子的殯葬與諸侯的殯葬相比較,規格高一些、隨葬品多一些無可厚非。但是如果諸侯的殯葬和周天子的一樣隆重的話,孔子就反對了。后人一說起厚葬,往往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孔子,認為孔子是中國傳統社會厚葬的“罪魁禍首”,這實際上是對孔子的曲解。 (二)以“禮”為核心 儒家提倡孝道,儒家殯葬倫理思想以“孝”為基點,同時還以“禮”為核心,把“孝”與“禮”結合在一起。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 孔子強調在父母的生前事后,都要嚴格按照禮節的規定行孝,不能有任何違禮的出現。正因為這樣,當宰我提出“三年之喪”為期太久的時候,孔子就憤憤然責備其“不仁”,說:“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孔子更明白地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由此可見,孔子所說的“孝”不僅僅是指內心的誠意,更是對先人體制與存在事實的尊重。就在這種尊重之中,孔子油然體會到“禮”的永恒莊嚴。 然而,盡管孔子主張以“禮”為判斷子孫是否盡孝的標準,但是,孔子倡導的這種殉葬觀念,客觀上卻為當時以及后世的厚葬風氣提供了理論依據。一方面孔子對于殯葬的“禮”沒有進行系統明確的闡述,對于其規范也沒有做出具體的說明,另一方面孔子崇尚周禮,對于周朝天子、諸侯等人的厚葬,非但沒有批評,而且還持一種肯定的態度,他只是反對僭越的厚葬,因而在孔子還活著的時候,厚葬之風就已經初露端倪。 《中庸》說:“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備亦。”儒家把“事死”和“事生”相提并論,并且認為只有做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才能仁智兼備。事死如生,長輩在世時要孝,長輩去世后,也要孝。長輩在世,子孫的拳拳孝心自然好表達,子孫是否盡孝,長輩本身就可以作為評判者。但是長輩去世后子孫的孝心如何體現呢?子孫是否盡孝需要依據什么標準來評判呢?又有誰來做評判者呢?在這種情形下,原本是表現形式的殯葬成為主要內容,殉葬的奢簡成為判斷孝的標準,是否合“禮”反而不重要了。 (責任編輯:悼詞文化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