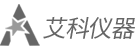|
首先,孔子從反面論證了服喪滿三年,則為孝。任意改動服喪期,比如把三年時間改為一年,就是不及。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乎稻,衣乎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亦有三年愛于其父母乎?”(《陽貨》) 宰我認為父母死后,守喪三年,時間太久。君子三年不去習演禮儀,禮儀一定會廢棄;三年不去彈奏音樂,音樂一定會失傳。陳谷子既然已經吃完了,新的谷子就會等場;打火用的燧木又經過一個輪回,一年也就可以了。孔子反駁他:“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便吃那白米飯,穿那花綢衣,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回答說:“安。”孔子搶白道:“你安,你就去干吧!君子的守孝,吃美味不曉得甜,聽音樂不知道快樂,住在家里不覺得舒服,才不這樣干。如今你既然覺得心安,就這樣干好了!”宰我退出來后,孔子說:“宰我真不仁!兒女生下地來,三年以后才能脫離父母的懷抱,替父母守孝三年,天下都是如此的。宰我難道就沒有從他父母那里得到三年懷抱的愛護嗎?” 從這段真實而生動的記載中,可見宰我是個獨立見解的年輕人。他不死守周禮,能夠反映時代潮流的走向,敢于提出以一年之喪,代替三年之喪,這是很不容易的。不過這種開時代新風的思想,卻遭到孔子的嚴厲批評。孔子首先沒有正面回答宰我的問題,而以一個比喻,表達他的觀點。 食乎稻,衣乎錦,安與不安的問題,是個常識性的問題,并不是宰我所問并需要解決的問題。他沒有想到教師會反問他這個問題,只好說:“安。” 孔子接著以肯定的口吻做出緒論說:“女安,則為之!”然后將辭鋒一轉,講到君子之居喪應該如何如何,認為宰我改革喪制的意見,是不仁。 孔子堅持三年之喪的理論根據,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實際指的是,初生嬰兒要吸取母奶或其他食物,發育為幼兒,必須經過三年時間,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在三年期間,母親對孩子的哺育和愛撫,極盡辛勞。人死服喪,是人的一種社會行為。這種行為的情和理,與子生三年不能離父母之懷的愛,有一定的內在聯系。但這種行為,畢竟是一定社會形態的倫理方面的表現,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與三年之喪密切聯系的,是“三年無改于父之道”。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張》) 孟莊子是魯國大夫孟獻子仲孫蔑之子,魯國的執政大夫,死于魯襄公十九年。孔子認為,孟莊子的孝行,其他方面都比較容易學到,只有他不改父親的家臣與生前定下的政治設施最難學。這表示孔子對孟莊子的敬佩。 對待這個問題,孔子不去具體分析,所謂父之道是包含什么內容的道,又屬于什么性質。如果父之道是正確的,或部分正確的,可以不改,或部分不改,如果父之道全是錯誤的,那就應加以全面糾正。孔子只將“不改”看作是孝,不問正確與否,這是不對的。例如,周初武王定下的政治設施,因武王早年死,周公攝政,同時發生的武庚與管叔、蔡叔之亂,而遭致破壞。如果周公不攝政、不平叛,怎么能行?周公雖然是武王母弟,非父子關系,但總不能說,他改前王之政,就沒有孝行吧。周幽王是個錯暴之君,被犬戎殺死驪山下,將老祖宗的基業都丟掉了。難道平王東遷洛邑后,不改其父之道,算是孝行嗎?孟莊子生前委用的家臣與定下的政治設施,應改與不改,要看具體情況而定,不能說,孟莊子全部不改,就是難能的孝行。 (責任編輯:悼詞文化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