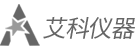|
、詞乃至書法成就來肯定沈氏的成就。 如果說生活于元曲這種文藝形式還未被廣泛認可、其地位還沒有完全確立的元代前期的鐘嗣成在肯定曲家及曲體時還不得不采取迂回方式的話,那么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滋蔓,元曲在歷經坎坷終于得到全社會廣泛承認且對人們的生活發生重大影響的明初,賈仲明在為曲家立傳時,再也不用“猶抱琵琶半遮面”了,而是直接從曲體本身來肯定曲家的成就。如《吊關漢卿》:“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對其地位、成就給予熱情洋溢的稱頌,沒有了鐘氏的繞彎子式的肯定。《吊高文秀》:“編敷演,《劉耍和》,……除漢卿一個,將前賢疏駁,比諸公幺么極多。”在與同類賢才的比較中,稱贊高文秀在劇作數量上的不讓眾賢。《吊馬致遠》:“戰文場,曲狀元,姓名香,貫滿梨園。……與庾白關老齊肩。”《吊王仲文》:“仲文蹤跡住京華,才思相兼關鄭馬。”在肯定挽吊對象的同時,流露出對關漢卿等曲壇英杰的仰慕之情。由此看出,賈仲明的時代,經過金元文人的理論倡導與創作實踐,以及舞臺形式的廣泛傳播,元曲這種藝術形式已經為人們所接受,其地位已經非鐘嗣成的時代所能比擬,在某種程度上說,它已經在藝苑站穩腳跟,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在肯定其價值時,用不著像元曲初興時那樣遮遮掩掩,要依傍正統文學去為它爭得一席之地了。 賈仲明對相關作家作了挽吊,在《錄鬼簿》卷尾道:“已上諸公卿大夫、高賢逸士鴻儒總括一篇:鐘君《鬼簿》集英才,聲價云雷震九垓。衣襟金玉名仍在,著千年、遺萬載。勾肆中般演就諧。彈壓著鶯花寨,憑凌著煙月牌,留芳名紙上難揩。”由在總體上對作家“著千年,遺萬載”的曲作成就的肯定,延至對錄存一代曲苑文獻的鐘嗣成《錄鬼簿》的高度贊揚,再到對雜劇勾肆搬演的稱頌,進而至于對曲家風流生活的激賞,可以說是對元曲作家、作品、演出、理論著述的全方位稱贊。這一方面說明明代戲曲創作環境之相對寬松,另一方面也說明戲曲的社會聲望在逐步提高,越來越得到社會的認可。從而,也為后人研究元、明戲曲的繁榮背景及相關問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考視角。 對一個生命個體、一種生命實踐方式的褒貶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評判者的價值標準以及所持的價值標尺。當然,在傳統觀念中,“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孔穎達疏云:“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其身既沒,其言尚存。”在與立德無緣、立功無望的情況下,“立言”便成了封建知識分子普遍而無奈的選擇。但是,這里所謂的“立言”,絕非指在曲苑說林舞文弄墨,戲曲家與小說家更是與所謂的“不朽”人生沾不上邊。鐘嗣成能夠一反傳統偏見,在元曲尚未得到社會認可的情況下率先為其振臂禮贊,為這些反叛世俗、蔑視傳統的作家立傳,認為他們同樣能夠流芳萬代。可以與“文章之士、性理之學”并傳不朽,成為“不死之鬼”,其膽識令人欽佩,其眼光讓人嘆服。然而,在慨嘆這些作家的命運時,鐘氏卻陷入了一種悖論之中。即:他往往以傳統的達兼標準來評判這些反悖傳統的作家,對他們“不屑仕進”、不為當政者所用的經歷、遭遇發出“志不獲伸”的感慨,流露出深深的惋惜之情;同時對其從事的曲作事業,則在某種程度上表示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惋惜。如《吊范子英》:“龍蛇夢,狐兔蹤,半生來彈鋏聲中。”對范以龍蛇自喻卻老死不偶、半生處境窘困而又欲有所干求、最終赍志以歿的遭遇寄寓深深的同情。《吊金志甫》:“夢西湖何不歸歟?魂來處,返故居,比梅花想更清癯。”對金氏似乎仕隱躊躇的矛盾痛苦深表理解。《吊黃德潤》:“風流才調真英俊,軼前車繼后塵,漫蒼天委任斯人。岐山風,魯甸麟,時有亨屯”。其“亨屯”在很大程度上是就其是否出仕、為世所用而言。《吊沈拱之》:“天生才藝藏懷抱,嘆玉石相混淆,更多世事碥破。蜂為市,燕有巢,吊夕陽幾度荒郊”。對其才學滿腹、困頓多舛、不為世用的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嘆康弘道:“恨蒼穹不與斯文壽,未成名,土一丘。”所謂“成名”,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出仕為官。吊周仲彬:“丹墀未叩玉樓宣,黃土應埋白骨冤,羊腸曲折云千變,料人生,亦惘然,嘆孤墳落日寒煙。”對其英年早逝、未能顯達寄予深深的同情。總之,鐘嗣成總把他們不被世用、終生受困看成是莫大的遺憾。聯系鐘嗣成“以明經累試于有司,數與心違”、“《鬼簿》之作,非無用之事也。大梁鐘君繼先,……累試于有司,命不克遇,從吏則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為喻,實為己而發之”的追求、經歷與遭遇看出,鐘嗣成與其他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很難在根本上從內心深處消弭對官場的依戀情結。而在《錄鬼簿》中,鐘嗣成把“前輩已死名公”列于卷首,并將他們的官職作了詳盡的羅列,聲言這些“前輩名公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樂府留心,蓋文章政事,一代典刑,乃平昔之所學;而歌曲詞章,由乎和順積中,英華自然發外者也”。我們當然不能對他這種作派多加苛責,但卻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體悟元雜劇是在怎樣的一種局面及作者創作心理的控御下艱難地發展,最終才走向輝煌的。另外,元雜劇的輝煌成就,體現在內容、藝術的諸多方面。就其內容來說,它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作了多角度的反映,這是人所盡知的事實。但以往在肯定作品內容時,往往注重其揭露黑暗、批判現實的一面,而對那些歌功頌圣、表現作者內心憂憤、發抒不為官場所用牢騷、宣揚教化、欽羨富貴功名等內容的作品缺乏客觀的審視與評判。讀了鐘嗣成這類吊詞,我們既可以體悟元代雜劇作家處境的酸辛,同時我們更能理解為什么他們在被統治者拋向了社會底層,卻還念念不忘表達為這個政權效力的熱情,還去殷勤地歌功頌德、宣揚教化,能夠加深理解元雜劇駁雜內容背后的復雜文化背景。 賈仲明則表現出與鐘嗣成迥然有別的思想傾向與取舍標準。賈仲明盡管也對元代曲家的遭遇時有述說,如說高文秀“早年卒,不得登科”,于伯淵“翠紅鄉、風月無邊。花前醉,柳下眠,命掩黃泉”,顧君澤“樂府共詩集開板刊,售文籍市肆停安。情恬淡,心懶坦,九仙在塵寰”,王守中“通街市,知假色,躲不了深土培埋”,王日華“璣珠梨繡,日精月華,免不得命掩黃沙”,劉宣子“填詞章,作樂府,登仕途,吏部遷除。熬年月,聽選補,淮東吏身卒”等等,但只是對作家生平遭際的一般性陳述,并未將他們仕宦不顯看做是特別令人遺憾之事。之所以出現這種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緣于賈仲明不同于鐘嗣成的人生追求與處世態度。如果說鐘嗣成是在“以明經累試于有司,數與心違,因杜門養浩然之志,著《錄鬼簿》,實為己而發也”的寫作背景下完成這部記錄一代文獻典籍的話,賈仲明則是在生活無虞的情況下自覺走上在曲作、曲評領域大顯身手、馳騁才情之路的。據《錄鬼簿續編》所載,賈仲明“天性明敏,博究群書,善吟詠,尤精于樂章、隱語,嘗侍文皇帝于燕邸,甚寵愛之,每有宴會,應制之作無不稱賞。……天下名士大夫咸與之相交……一時儕輩,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他以文學侍從的身份優游于燕王府邸,晚年自號“云水翁”,并以“怡和養素軒”命其居室,可見其處世態度與恬適心境,以及對官宦仕途的淡漠。換言之,正由于賈仲明這種生活態度與價值取向,決定了他在憑吊曲家時,沒有更多地根據是否顯達去給他們定位,而是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在他們的曲作成就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