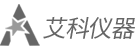|
唐五代及北宋描寫婦女的詞篇,多數境界狹窄,詞語塵下。蘇軾此詞境界開闊,感情純真,品格高尚,讀來使人耳目一新。用詞來悼亡,是蘇軾首創。在擴大詞的題材,在豐富詞的表現力方面,本篇應占有一定的地位。 本篇完全可以同潘岳的《悼亡詩》,元稹的《遣悲懷》以及南宋吳文英的《鶯啼序》前后輝映,相互媲美。 補充: 蘇軾十九歲與同郡王弗結婚,嗣后出蜀入仕,夫妻琴瑟調和,甘苦與共。十年后王弗亡故,歸葬于家鄉的祖瑩。這首詞是蘇軾在密州一次夢見王弗后寫的,距王弗之卒又是十年了。生者與死者雖然幽明永隔,感情的紐帶卻結而不解,始終存在。“不思量,自難忘”兩句,看來平常,卻出自肺腑,十分誠摯。 “不思量”極似無情,“自難忘”則死生契闊而不嘗一日去懷。這種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怎么也難以消除。讀慣了詞中常見的那種“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柳永)的愛情濃烈的詞句,再來讀蘇軾此詞,可以感受到它們寫出不同人生階段的情感類型。前者是青年時代的感情,熱烈浪漫,然而容易消退。后者是進入中年后一起擔受著一生憂患的正常的夫妻感情,它象日常生活一樣,平淡無奇,然而淡而彌永,久而彌篤。蘇軾本來欣賞“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的藝術風格,這首詞表達的感情就是如此,因此才能生死不渝。 此詞還有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即這次夢中的夫妻相會,清楚地打上了生死之別的烙櫻夢中的王弗“小軒窗,正梳妝”,猶如結縭未久的少婦,形象很美,帶出蘇軾當年的閨房之樂。但是十年來的人世變故尤其是心理上的創傷在雙方都很顯然。 蘇軾由于宦海浮沉,南北奔走,“塵滿面,鬢如霜”,心情十分蒼老。王弗見了蘇軾,也是“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似乎在傾訴生離死別后的無限哀痛。生活的磨難,對于無意識的夢境,同樣起著潛在而深該的影響。末了三句設想亡妻長眠于地下的孤獨與哀傷,實際上兩心相通,生者對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本文來自吊詞悼詞文化網 www.701621.com 非常欣賞蘇軾的這首詞。想象著蘇軾夜半拭淚醒來,仍恍如不知其妻王弗是真的香魂歸來或者只是一個夢? 真的只是一個夢嗎? 那般地對鏡理紅裝,那般的淺笑盈盈,竟只是十年前的片段?那般的那般又是何時深植于這物逝飛快的十年記憶的呢? 于是蘇軾微嘆了口氣,滿復愁思只換作輕輕地道出:十年生死兩茫茫…… 愛情與死亡是永恒的主題,尤其是有著死亡段落的愛情。 老Rose握著“海洋之心”站在曾經吞噬Jack的霧海上,回想當年劃破冰海之夜的字字句句,想說的,只有“十年生死兩茫茫”;38歲的渡邊在飛機上偶爾聽到Beatles的《挪威的森林》,想起曾在直子腦后的發夾,念叨的,也只有“十年生死兩茫茫”;陸游如果路過唐琬的墳墓,“錯,錯,錯”已毫無意義,不如插上一支白菊,嘆一句:“十年生死兩茫茫”;等到痞子蔡有家有室之后,每次喝到咖啡,想起那個一身brown的舞者,腦中浮現的也應是“十年生死兩茫茫”;至尊寶會一直記得那個一身嫁衣含恨而逝的紫霞,會忍著心頭劇痛而說:“一直有份真摯的感情擺在我的面前,雖然是十年生死兩茫茫。” “十年生死兩茫茫”,曾經相濡以沫的愛人永隔陰陽已經多少個黃昏,思之不得見之,念之不得語之,只留得記憶中殘存的歡景愉時,當作泡過千次的茶,反復溫習著熟悉的味道,憑吊十年前的紅袖添香;“十年生死兩茫茫”,“茫茫”的何止“生死”,十年了,一切皆“茫茫”,皆“今非昔比”了。也只有這份感情沒有“茫茫”而去了,即使死者已逝,但生者永記,在每個月明相思之夜,不思量間,自會神回小軒窗,自會腸斷短松崗,思念、無奈、悲切、感慨,一句“茫茫”,訴盡心事! 至尊寶帶上緊箍咒前曾經問過觀音姐姐,為什么恨一個人可以幾十年幾百年地去恨,其實愛一個人也可以幾十年幾百年地去愛。 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茫”,讓我在過往與現時的紛亂迷離中看到一滴可以保存千年的眼淚,看到一朵香墳前不敗的白菊花。 (責任編輯:悼詞文化網) |